夜露轻易打湿了我的眉发,将落不落地低垂,冷成一绺绺刺寒的冰,锈在我两颊。更深露重,原来是这么个来头。
冷晖枪不敌晚风凌厉,湿寒刺透骨髓牵动脉血,枪尖滞缓,难从白日里的自如,每出一回都不尽人意,甚至显得短笨不堪。一名士卒觉出状态不对,几步上来叫停,就领着我往军帐去休息。
厚帐严严实实一遮,再有厉风飞沙也寻
不住踪迹。帐内出奇和暖,眉间一痒,是冰棱化水淌下睫羽。我目光不转,任由它落。帐内坐着的军师心神也定,摇扇同人添茶,我心领,静静当根门柱,杵在帐帘边,顺带着让筋骨缓释过来,一时间极静默。先是军师的客人察觉到有人在,他放下茶盏一侧身,光随影动,额间碎发投下薄薄一层影,眉眼笼于其间,目中波光却不减,像一潭黑泉。他眼底清冷,望向我时也未有神色浮在面上,气息敛得极轻,衣褶不动分毫。

这面貌我怎会不认得,我以枪为械,他以我为械,我如今的形状,全是凭他的言行意愿一刀一刀刻成的。我紧盯着这张脸,皮肉柔和,它之下包裹着的魂骨早该灰飞烟灭了。但他不是什么魑魅魍魉,我不愿信神鬼,只道这是一场将终的乱梦。我定下心神等自己醒来。须臾,烛火的暖意融进一片黑中,人物的形与容如同潮水退却,实感也随之急急消散,我有些惘然,看得不很真切时,那军师残有的面影却忽而开了口。
梦中惊起,太阳穴被混作一团的冷汗热汗浸得发胀,枕巾早已湿透。小卒见着我醒了,端着一碗还温热的汤药上前问,我脑中沉闷,神志还不完全清楚,只管摆手推了药碗,翻身下床要拾枪,腕间筋骨被牵扯得即刻一凛,隐隐抽痛起来。我掰直手腕,忍着酸胀抚抚枪杆,预想中的踏实感并未到来,只能勉强想起梦中的军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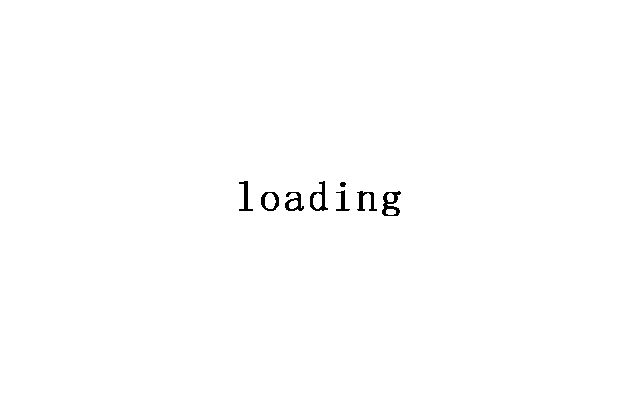
冷晖枪不敌晚风凌厉,湿寒刺透骨髓牵动脉血,枪尖滞缓,难从白日里的自如,每出一回都不尽人意,甚至显得短笨不堪。一名士卒觉出状态不对,几步上来叫停,就领着我往军帐去休息。
厚帐严严实实一遮,再有厉风飞沙也寻
不住踪迹。帐内出奇和暖,眉间一痒,是冰棱化水淌下睫羽。我目光不转,任由它落。帐内坐着的军师心神也定,摇扇同人添茶,我心领,静静当根门柱,杵在帐帘边,顺带着让筋骨缓释过来,一时间极静默。先是军师的客人察觉到有人在,他放下茶盏一侧身,光随影动,额间碎发投下薄薄一层影,眉眼笼于其间,目中波光却不减,像一潭黑泉。他眼底清冷,望向我时也未有神色浮在面上,气息敛得极轻,衣褶不动分毫。

这面貌我怎会不认得,我以枪为械,他以我为械,我如今的形状,全是凭他的言行意愿一刀一刀刻成的。我紧盯着这张脸,皮肉柔和,它之下包裹着的魂骨早该灰飞烟灭了。但他不是什么魑魅魍魉,我不愿信神鬼,只道这是一场将终的乱梦。我定下心神等自己醒来。须臾,烛火的暖意融进一片黑中,人物的形与容如同潮水退却,实感也随之急急消散,我有些惘然,看得不很真切时,那军师残有的面影却忽而开了口。
梦中惊起,太阳穴被混作一团的冷汗热汗浸得发胀,枕巾早已湿透。小卒见着我醒了,端着一碗还温热的汤药上前问,我脑中沉闷,神志还不完全清楚,只管摆手推了药碗,翻身下床要拾枪,腕间筋骨被牵扯得即刻一凛,隐隐抽痛起来。我掰直手腕,忍着酸胀抚抚枪杆,预想中的踏实感并未到来,只能勉强想起梦中的军师。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