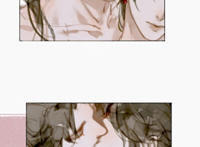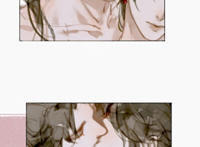“怎么样都可以?”
被捏了下巴的美人睁开眼睛,低眉颔目,又眼波流转。四目相对,坚定而悠远。
乌溪把景七扶起,从背后的柜子里取了薄木板,扔在景七怀里,“抱着。”景七苦着脸接过来,桃花眼里满是祈求,乌溪权当做没看见,一路拉他进卧室。
卧室里点着蜡烛,火光微弱,刚刚够看清人脸,乌溪接过板子扔在床上,又把人剥得只剩最里面一件薄如蝉翼的纱衣,长度到大腿中间,其他什么也没给他留。
“乌溪……”景七感受到了浑身的凉意,突然觉得有些紧张。
没有回应。乌溪也脱了外袍,取下了丁零当啷繁琐复杂的南疆饰品。怕乍一褪衣有些凉,便抱住景七,把自己的温度渡给他,双手环在他后腰,卸下手上乱七八糟的指环。而后右手食指和中指指尖抚上景七脊背,顺着脊柱曲线轻轻往下划,叼着人耳垂,在人耳边含混地说:“你最近不听话太多次了,今晚不可以再违逆我,一次都不可以。”
身经百战的景北渊居然体会到了乌溪被他弄得五迷三道的感觉,他呼吸有些急促,晕乎乎地回了声好。
话音刚落整个人就被垫了软垫按在了桌子上,景七刚反应过来想挣扎下起身,便被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压了回来,身后那人俯身把话一个字一个字说进他耳朵里:“没听懂我刚才说的话?今晚不可以再违逆我。”声音不辨喜怒,却低沉有磁性。
罢了,他怎么样都可以。
虽然景七不再反抗挣扎,但按着景七腰的手也没松开。乌溪另一只手往景七身后落巴掌,斜向上的力道带的整团肉随着手掌颤动,景七试着不让自己惊呼出声。